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縫!現就縫!」
始用命令逼迫,即使針尖扎破,血染臟布,只扔,定再次塞回。
拿起笸籮里剪子將布剪支破碎,穆懷川干脆把將子掀倒,格沉。
隨后把捏腕將直接提起,盯著,橫。
「祁祁祁,祁兒嗎?被囚牢里,原本留全尸,但現。
既然阿姊麼著,就斷條胳膊阿姊拿以解相!」
,傷害祁。
連忙拽穆懷川胳膊,祈求向。
「別,縫……就縫。」
著跪散落針線布,布被剪支破碎,毫猶豫剪自己條袖。
顫,線麼都穿過針。
穆懷川著卑微模樣,卻更惱。
蹲撿起破碎布角放到面,帶幾分。
「,今事就像布樣,破再也補回。
罷起,疾沖到面將,就似與瘋話般,瘋狂點。
「能補回,塊布能補回!」
「次般,與,就算補回,也原先張,修補永都修補,永都裂痕。」
穆懷川著抬撫角處傷疤,摩挲。
斂眸放姿態,「奴錯。」
「既然錯,就受到懲罰,就朕貼女官吧。」
「好。」
穆懷川后,就像瞬被抽空力樣跌,直到果扶起,才漸漸回神。
穆懷川貼女官,就與以照顧般無異,龍案批奏折,便端茶倒。
咳,就旁揉肩,漸漸移到后頸,恍惚些神。
對沒防備,現完全以直接擰斷脖子。
「每都數盡奏折,面些個個就像喂飽饕餮,煩。」
穆懷川忽然抱怨,而后沒好將奏折扔到邊。
忽然被覆,握著揉捏,又將拉到面,個埋懷,雙環抱著腰。
子隨之僵,握拳又松,才將推作克制。
「……見……阿姊,阿慎好累。」
呢喃著,將放頂。
僵頓片刻,才順著緩緩撫摸而。
似乎很滿,故往腰吐,燙得緊。
松將拉到懷,仰用尖蹭著,眸半睜,線脖回流轉,就像野獸到滿玩物,用尖爪子夠試探。
直到拉著解腰腰帶,終于忍抽回起逃,卻被把拽回腿。
「逃什麼……害羞?」
轉將抱壓榻,似乎方才逃作,拒絕而欲拒還迎。
欲吻,連忙偏,用力把推后,識從龍案摸起硯臺當反抗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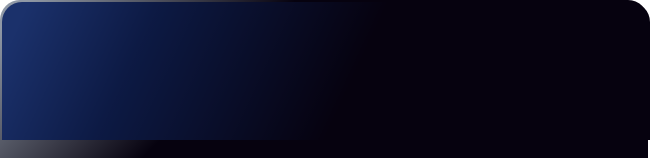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