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自就習慣暗詭譎,樣角力廝殺對而言就像飯樣平常。
越樣越讓疼。
否從曾過個好,過完全放飯菜……全全過個。
盛景堯似乎唏噓,笑,冰皇,笑都幾分純粹。
「阿,沒過為殺👤,第次見殺👤嚇成樣。」著又拉起,細細摩挲:「怪,讓也沾血🩸……」
忍又酸:「也沒到放棄皇位,受盡苦楚才到個位置……」
搖搖:「因為終于,只個位置,對就遲變成傷刀,賭起百密疏。」
「再者,位置太,幾得失,已經后悔……阿,從直讓皇后,把世最好都捧到面,后現,只讓妻子。
盛景堯總藏起自己,如今終于敞扉,幾句話就將顆扔滾油之,又燙又痛,淚簌簌而。
「之為何從對,些事……」
皺眉,分抗拒:「,些事當真相,過后再就狡辯。還些腐爛臭恩怨,丁點都讓。怕需用更,至輩子回,也愿等……」
著又哼:「福澤對忠耿耿,還替次葬份,就敢自作主張把個匣子拿,就狠狠罰!」
呼:「對,盒墜子!」
「帶。」
盛景堯柜子里拿個匣子卻,底浮淚:「阿釀酒,壇酒換只墜子。」
恍惚,又同當個酒肆后院,掏對墜對只只留著起,好像久。
后,桃面,還。
笑著點點:「好,壇『兩相』換只墜子。」
盛景堯驀睜,半晌才步過將抱懷里,親密無,再也沒隔閡。
事已,懷抱猶,此后經余,唯愿與君同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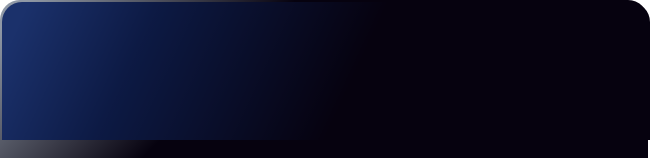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