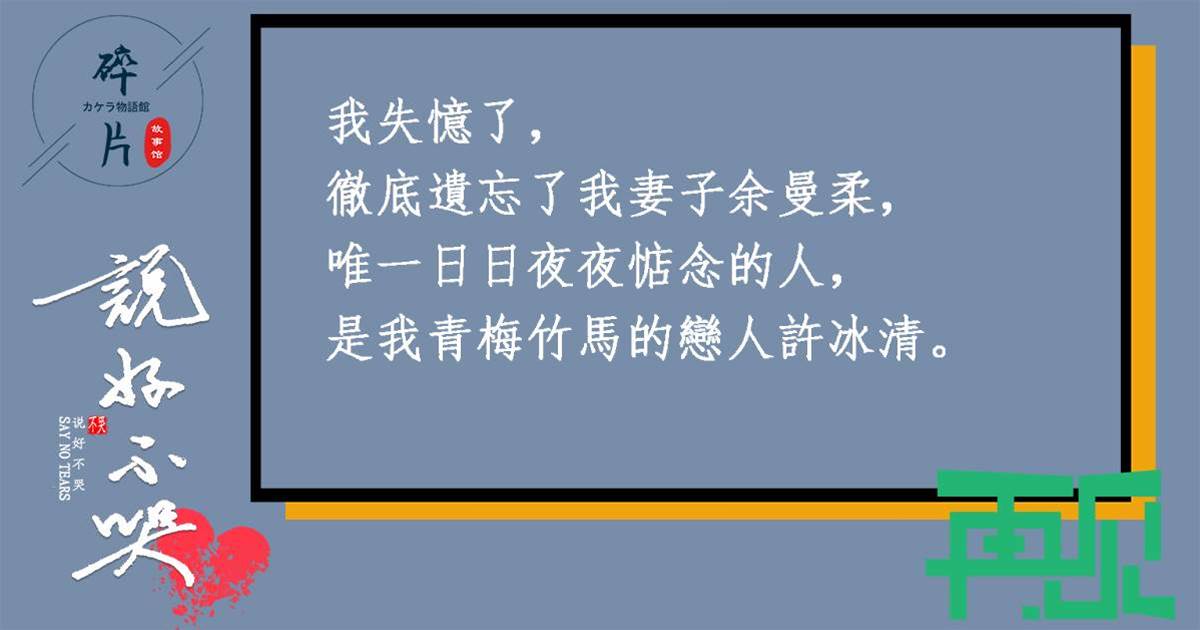《獨家記憶》第12章
ADVERTISEMENT
到刻,終于承認,余曼柔里并無。
捂著,能再,再勉自己。:“冰清,。”
交換位置候,摔跤,跤并嚴,許冰清卻嚇壞,扶起,拿起腕,面皮磨破點,疼:“疼疼?”
疼嗎?當然疼,算什麼呢,禍差著萬千里呢,只摔跤,只磨破層皮,而,余曼柔,把自己撞。
為什麼麼難受,種細微像蟲咬向全擴散著。
自問,余曼柔里嗎?,從得對憐、愧疚,絕沒過對,直到此,理智依然認為對。
ADVERTISEMENT
猜你喜歡
溫馨提示
加入尊享VIP小説,享受全站無廣告閲讀,海量獨家小説免費看
進入VIP站點

 上一页
上一页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